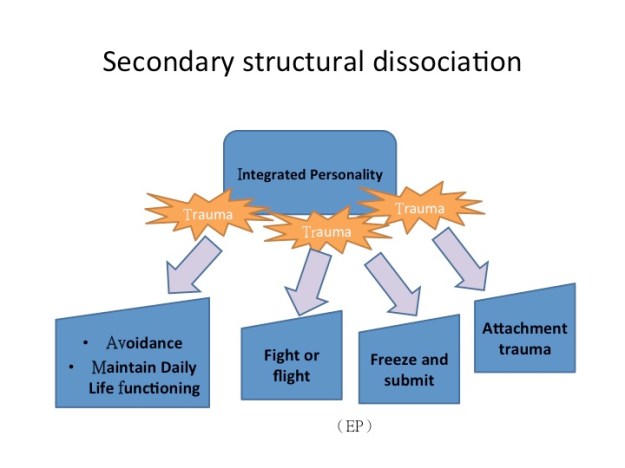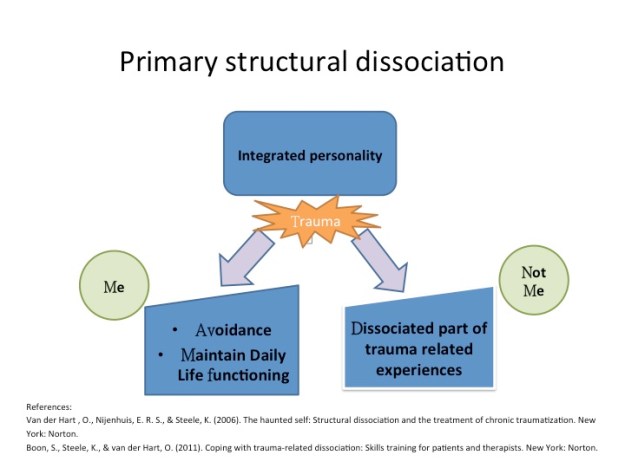文字:胡嘉琪博士
每次在太平洋兩岸往返,我總是會遇到飛機上和機場裡的爸爸媽媽和小孩。有一件我覺得很可惜的事情是,亞洲很多父母不讓孩子自己吃東西。
我在台灣看到很多爸媽都會喂小孩,這一點,我們家爸媽就是追著孫女餵的爺爺奶奶。而我小時候據說也是這樣被餵大的。
可是,我在美國,確實看到,很多孩子,不管是一歲半還是兩歲,肯定自己餵自己。
小孩即便是用手抓著吃,也是自己吃。父母做得就是準備好不會讓孩子噎著又有營養的食物,幫孩子綁好圍巾,預防食物弄髒地毯,就這樣,放手相信孩子可以自己餵自己。
這樣的相信,既簡單又困難。畢竟,大人做事情肯定比小孩自己來還要有效率。父母要忍住自己想幫忙的衝動,還得應付讓小孩自己吃飯,食物可能掉得滿地的多餘家事。
但同時,這樣的相信,既簡單又深遠。
人是怎麼發展出對自己的自信心的呢?就是從這麼小開始。小寶寶要用力伸出手,試著精準地拿起一塊蘋果,然後再對準自己的嘴吧塞進去。如果有學習寫 AI 人工智慧的人,就知道,光是寫程式訓練一個機器人做這些事情就不容易了,那麼,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小寶寶要動用多少的大腦神經與身體肌肉神經,才能完成這樣一個看似簡單卻又困難的任務呢?而完成任務之後,小寶寶對自己和對這個世界,會培養出多大的相信呢?
今天發現,我很喜歡的王理書老師,她有本書今年在中國內地出了簡體字版,書名就是,「媽媽,你慢慢來:信任孩子的尺度」。這本書在台灣的書名是:「這樣守護孩子的心靈自由」。
我很欣賞簡體字版的書名,我讀王理書老師的文章與書籍十幾年來,我真的覺得理書老師是一個懂得如何信任孩子的媽媽,這不是一般相信孩子會自己把功課寫完的那種信任,而是真心相信每個孩子都能長出獨特自我的相信。
因為這樣深的信任,理書分享如何與孩子相處的故事,都散發出一種很自由的感覺。
今年去北京上課,記得有學員給我的回饋是,我那說話時自由的身體讓他們回想起,自己也曾經這麼自由。真好,那我們就一起來學習怎麼當可以給孩子自由的媽媽吧!
自由與責任其實是手牽手的朋友,我好佩服理書老師在書中分享各種讓孩子對自己生命負責任的相處秘訣。例如,理書老師在書中提到,訓練孩子做家事,其實從兩歲就開始囉,這也呼應上面我提到的,兩歲就讓孩子自己餵自己吃飯的「家事」。而如果孩子到了五歲還沒有培養出做家事的習慣,那之後就要傷點腦筋才能改變這樣的習慣了(這就是我們家兩個青少年的狀況啦~~~)。
只是,兩三歲的小娃娃,能做的事情很多也很少。這麼樣大家彼此學習討論出適合早期孩子發展的家事,那就是一門很難的藝術了。
把餵自己吃飯以及做家事,當成跟考一百分一樣是值得榮耀的事情,
那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
能夠負責任照顧自己的孩子,
長大之後能夠探索的世界才更廣,才有更多的自由呢!